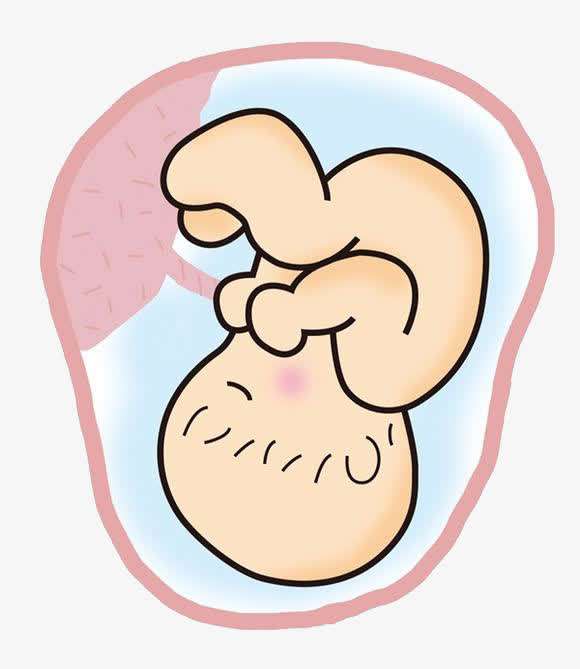代孕,你真得清楚吗?
“希特勒就曾开发过一款无与伦比棒的轿车,”斯卡利亚说道,“但那又能证明什么?我可以跟你拍胸脯,即使你改用另一套理论,你一样可以斩获一些理想的结果。但这不是考验所在。真正的考验在于从长远计,整个社会究竟是按照宪法里白纸黑字拟定的章程来运作,还是光凭九个法官的一面之词来定乾坤?”
——安东宁·斯卡利亚[.]
一、引言
去年,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涉非法买卖卵子并委托他人代孕的案件。案件基本情况是:A男与B女均为再婚,因B女患有不孕不育症,故两人决定通过体外受精及代孕的方式生育子女。事情按照两人的安排顺利进行,通过A男的精子与购买的卵子受精结合形成受精卵,进而寻求某一代孕女子通过医疗技术人工着床受孕,并于2011年顺利生产一对异卵双胞胎。天有不测风云。A男于2014年患病去世,孩子则随B女生活,直到A男的父母起诉B女,请求法院将监护人由B女变更为老两口。
审判过程中,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通过DNA分析结果得出鉴定意见:B女同孩子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但不能排除A男的父母其同孩子之间祖孙血缘关系。
对此,B女主张,孩子一直由她抚养,应推定孩子为她的婚生子女,即使无法推定,也应该视为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
案件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诉述,一审法院判决孩子的监护人变更为A男的父母。B女进而提出上诉。从案件本身来看,这是一个民事领域的疑难案件,面对法律文件禁止的买卖精子、卵子以及代孕行为,司法审判中究竟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更为困难的是由这一系列行为引发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变动与消灭,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
根据相关的民法原理,父母同子女之间关系自胎儿出生时开始产生,看似严丝合缝的法律规定却具有巨大的开发性,何为出生已经有不同的学说,而何为母亲这种“天经地义”的认知也被冲击,以此案为例,就存在生物学母亲(提供卵子者)、孕育母亲(提供子宫者)以及争夺监护权的抚养“母亲”(事实养育者)三者的区分。任何一方都有自圆其说的理由。生物学母亲可能主张基因、血缘为主,其提供了最原初的基因,孕育幻化的开端从卵子中汲取;孕育母亲可能主张十月怀胎的艰辛以及经由脐带联结的同呼吸与共命运的血脉与感情;而抚养“母亲”则主张辛勤与情感的付出,或者说这是一张“感情牌”。究竟哪一方的理由更加充分并不在于这一方的理由具有压倒性或高度盖然性,而是审判者以及案外人所持的立场。
跳出这个案件具体信息本身——理论意义往往更大——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家庭纠纷案件,这更是一个法治的侧面或缩影。并不是说,这个案件不重要,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说,这也许就是其生活的全部,抽象出来的理论意义离他们太遥远而无法切身感知。
二、代孕与审判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便利了医学代孕的发展,从取精、取卵、体外受精再到受精卵的人工着床已并非特别困难的医学技术。代孕并非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前述代孕更多的是指医学代孕,笔者在进行某项社会调查的过程就发现了埋藏在社会角落之中的代孕——借种生子。
大约在1952年的时候,张某男因自己检查出不育,便请丁某男同其妻子发生性关系,后怀孕生有一子,为此整个村庄到现在都有人拿这件事讥讽他们一家人。在医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当时,张某男在强烈的求子观念引导下采取了“代孕”的方式,幸运的是并没有发生监护权纠纷,这并非个例,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代孕案件,不同于前述借种生子,这是一件借腹生子的案件。雷某男是当时的地主,因其妻子一直不孕,在征得自家长工以及长工妻子的同意下,其同长工的妻子发生了性关系,生育的孩子归雷某男,相应的条件是怀孕期间的费用由雷某男出,并且多付给长工一年的工资与两袋地瓜干、半袋小麦。
这两个代孕事件与闵行区法院审理的代孕案件既有相同点,也有很大的区别。相同点是几者都冲击了所在社区的传统秩序,引发了相应范围内的争议。不同点是闵行区法院审理的案件出现了纠纷,进入了诉讼程序。
而笔者调研村庄的代孕事件随着时间的推演,逐渐为人们淡忘,并且在事件发生村庄也充斥着一种同情的论调,“想要个孩子而已,虽然听起来不光彩,也无可厚非,只要双方同意谁也不能说太多”。在信息传播与舆论泛化的当下,这类事件——特别是同道德争议相关的——不断引发着公共性扩大的问题,这种泛道德化的考量的大量存在导致了我们习惯性的将任何事件都予以道德化。
闵行区法院审理的这个代孕案件更多地反映了以审判为符号的法治与代孕为符号的科技的冲突,而非与代孕为符号的道德的冲突。因为“我们如果有足够的知识,我们在法律上的许多道德两难就会消失。如果我们确知上帝存在,确知上帝强烈谴责人工流产,那么关于人工流产的辩论就会结束。……在一种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道德辩论会最为激烈;因为人们缺乏可以客观复制的知识时,他们就会退守,依赖扎根于个人心理和教养的直觉以及个人的经验。”[,TheProblemofJurisprud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转引自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09页。]大多数人拿过这个案件并非探讨案件依照法律程序究竟该如何处理,而是讨论代孕是否道德,毕竟谁都可以说两句。即使是法律人在讨论这个案件时也不免落入道德议论的窠臼。
并非说这个案件同道德争议无关,正如我们所深深嵌入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道德争议。只是在道德争议之外,或某一刻我们考量道德争议的时候能否保持必要的理性。职业角色的定位让法官依照法律进行审理,这并不能成为一些人批评法官的理由,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审理这个案件的是作为法律符号的法官这一职业,而不仅仅是某个具体的法官;其次,才是这个具体的法官。如果法律是法官用来穿着的法袍,作为一种符号其具有两种基本作用:第一,让法官穿进去,给他予以必要的限制;第二,作为一套服装发挥保护作用。如果法官没有这样一套衣服给予必要的限制和保护,不仅会导致司法权的膨胀,同样可能基于道德争议的挤压导致司法权无限度的扁缩。我们既不能纯粹的认为法官是运转机械原理的“售货机”,同样不能认为司法判决乃是法官的任意遐想。
三、原旨主义解读
绕开法律纠纷以及本身的法律问题以外,不可避免的要进入道德领域,“诸神之战”在所难免,导致一种“共识危机”。在伦理学的知识谱系中,直觉主义与情感主义这两种不可知论的伦理学立场往往被指责为制造社会“共识危机”的罪魁祸首。[王彬:“法律论证的伦理学立场——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33页。]达成共识往往是问题或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
会受到质疑的是:即使司法达成裁判,也未必见得在本案中会形成共识。从表面看,司法裁判中往往会出现原告被告都不服的情形,输了的上诉想赢,赢了的也上诉想赢更多,怎么能算作达成共识呢?在具体纠纷的争议上的确很难达成共识,也无需达成完全的共识。在表面之后予以支撑的是稳定、明确以及理性的共识——法律,实际上就已经充当了深层的共识标准。
道德同法律相比,其稳定性、明确性都要松散的多,从内涵到外延都极大的存在移动可能。人们往往借助道德语言做出道德判断,但道德语言的本质不在于指称事实,而在与影响人们,他们只不过表达或激发了判断主体的情感或态度。[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法律并非是对本案具体纠纷所涉及的道德争议的标准,是长时期共识的结果,法律并不具体介入该案的道德争议,仅提供一种功能性的途径。虽然法律通常会切合该案具体所维护的价值,以及出现同道德话语重合的情形,但不能因此将法律道德化,消解其自身的独立性。任何一个司法案件的出现,都会涉及相应的法律,法律的效用在于提供解决手段,而非为道德争议提供话语权工具。在司法实践中,将法律放入道德争议之中,并不能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官方话语消弭道德争议的缝隙,相反可能导致道德话语削弱法律的正当性基础。
由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谨慎的遵守现有法律的规定,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法官造法”都应该谨慎对待。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与第22条(禁止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手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3条与第7条(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以及《民法通则》第7条与《合同法》第52条规定(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首先医疗机构不能实施代孕手术,那么非医疗机构以及个人是否能够实施代孕手术?作为器官的子宫不能进行买卖,是否可以有偿使用?以及精子、卵子与受精卵是否是器官?
部分人主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一个部门规章,并非法律,根据《妇女权益保护法》第51条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妇女(公民)享有生育权。作为部门规章不能限制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并且依照《立法法》第7条规定,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所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仅能限制医疗机构。但实际上,除医疗机构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并无资质开展医疗技术服务,相应的医疗器械更有国家严格管控,私人很难开展代孕手术,并且根据计生条例,国家禁止“非婚生育”,通过性交方式的代孕也违反法律。则即使依照支持者的观点赞成非医疗机构即可实施代孕,也不具有现实意义,仅存在理论探讨空间。[参见杨遂全、钟凯:“从特殊群体生育权看代孕部分合法化”,载《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
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3条与第7条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不禁止人体器官捐赠,对于本案而言,不存在捐赠情形,A男与B女是通过共计花费80万的成本寻求第三人的代孕,所以对于该条值得争议的是精子、卵子与受精卵是否属于器官。持扩大解释观点的人认为,即使精子、卵子不能视作器官,但受精卵仍可以被视作器官,同其他器官一样,受精卵置于活体环境完全具有发育为胎儿的可能性,不能仅因为受精卵的体积与形状予以否认。

对于本案而言,争执受精卵是否属于器官的的意义不大。根据《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规定,对于精子的采集、供应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从采集、供应的单位设置,再到向医疗机构的供应,甚至规定了每名男子最多向五名受孕妇女供应精子。第一,代孕行为中存在买卖行为的是A男购置卵子同其精子结合,以及代孕母亲的代孕过程,而受精卵由A男转移到代孕母亲,可视作捐赠的形式,这并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第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监护权,即使买卖受精卵是一种买卖器官的行为,受精卵已经发育为胎儿并出生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既不能没收亦不能销毁,这同其他器官买卖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在司法实践中,“非婚生育”受到法律的禁止,但分“非婚生育”的婴儿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所谓“孩子是无辜的”,“非婚生育”的违法性并不延伸到非婚生育的孩子身上,通过法律的方式切断了违法的牵连性。
《民法通则》第7条与《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对代孕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代孕明显违背传统的生殖繁衍理念,有违公序良俗。实际上,对于公序良俗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差异,何为公序良俗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是在边缘结构[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同时也存在于其中心结构。[参见蒂莫西·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社会公共秩序以及良好的社会风俗可以掺擦大量的异样理解,不仅对这些词语的本质所指称的事实的理解上有差异,对于“社会公共秩序”与“良好的社会风俗”词语本身也存在理解差异。进而引发了我们在理解这个词语时必须依赖整体、体系以及语境,再涵摄到这个具体的案件上。《合同法》第4条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而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由法律规定,进而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有对自己生育权进行处分的权利,当事人当然可以签订代孕合同,对自己的生育权进行交易。由此不仅需要看到《合同法》第52条所涉及的公序良俗原则,更要看到本法第4条明确规定的合同自由原则必须予以体系化的考量。
四、结语
2015年底进行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在法律草案中明确禁止代孕,但在法律最终通过以后又删除了这些条款。对此,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予以解释说是因为代孕规条起草时间紧张,与会人员争议较大,最终没有通过。这也反映了对于时代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出现分歧,这也反映了价值多元时代人们对于价值本身思考的多样性。
但对于法律本身而言,如果现有法律并未发生更改,仍需要依照目前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判。舆情讨论引发的争议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标准,否则不免陷入“广场式司法”的窠臼之中。同样,法治也不能忽视民意。法治回应民意的方式不仅有司法的方式,在法治建设中存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多环节。对于舆情民意出现的争议,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善谈民主以及代议契约等形式予以程序化吸纳的方式。但就本案而言,仍应坚守司法的谨慎与原旨主义。
标签: